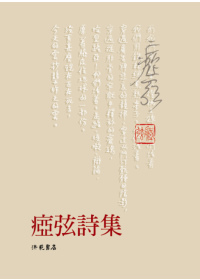想拎一首詩幽默地行過兩個夜夾著的深淵
文╱李進文(詩人、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)
去年(2013)五月,瘂弦返台配合拍攝「他們在島嶼寫作Ⅱ」紀錄片《如歌的行板》。當日,拍完後免不了《創世紀》詩社同仁要聚聚,餐後我們在台北某間茶館歇下,瘂弦、張默、辛鬱、管管一夥《創世紀》前輩詩人在茶餘飯後打開前塵往事的話匣子,聊起年輕時的感情八卦,矛頭忽地指向瘂弦,他淡定中見招拆招,以幽默,呵呵朗笑道:「人生這麼長,怎能不有點事兒呢?」
有同仁回想起當年瘂弦在學校給學生上課,那具有廣播人特有的磁性嗓音,字正腔圓,咳唾成珠玉,人又帥氣俊挺,「ㄟ~ 你是不是盯著講台下很多女學生放送愛慕的眼神?」瘂弦答道:「不,我都盯著教室後面的『禮義廉恥』四個字。啥事也沒有。」
起鬨的話題,在愛情上溜轉,他妙語珠璣,舉某藝術家詩人說的一句話:「成功的愛情一定包含兩點:一是勇於表達,二是容易脫手。」又道,「世界上最細緻的事,有兩件:一是政治,另一是愛情。」然後對著在座最年輕的我說:「你們這一代,詩很穩健,愛情表現差了點……以前我們只要一個眼神,一聲咳嗽,就知道愛情發生了;現在你們愛情發展了半天,結果卻什麼也沒發生!」同仁女詩人古月則嚷道:「瘂弦你的紀錄片要講這些(感情八卦)才精彩啦……」瘂弦瞇眼養神,一副雲淡風輕。
今年(2014)九月,我終於看到紀錄片的試映,想起一年多前,那次同仁聚會時瘂弦的「愛情」妙語,私心想看看紀錄片中有關瘂弦的情感世界。片子中,我確實看到,我看到瘂弦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家中仔細整理、輕撫著已逝妻子張橋橋娟秀字跡的信,我看到他訴說種種對橋橋的回憶。畫面有一幕讓我熱淚盈眶,他帶著女兒坐在橋橋的墓前草地上,鏡頭晃過墓碑,我看到碑上鑴刻著的不是孤伶伶的一個名字,瘂弦的名字也在其上,死生相伴,摰愛不渝,看他凝視著墓碑,是否想起他寫的〈給橋〉:「常喜歡你這樣子/坐著,散起頭髮,彈一些些的杜步西」瘂弦的愛情,整個都在橋橋的身上。
談瘂弦的詩,為何講起愛情?不,我是認真要談詩,談詩要先談詩人的「態度」。我始終覺得瘂弦的詩,最深刻的是來自於「幽默」態度,而不是意象或他反覆為人稱道的「音樂性」節奏。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對愛情這樣一個不容易幽默的題目談笑風生,一旦轉化為〈給橋〉,「下午總愛吟那闋『聲聲慢』/修著指甲,坐著飲茶/整整的一生是多麼長啊」,遂成了深情而日常的語聲,這時幽默還是節制著的,在〈水手.羅曼斯〉真性情豁起來了,「今天晚上可要戀愛了/就是耶穌那老頭子也沒話可說了」、「快快狂飲這些愛情/像雄牛那樣」、「女人這植物/就是種在甲板上也生不出芽來」這是寫水手對於愛情的渴望和追求,節奏飆起來了,帶動詩人本性,幽默感往往比險奇的譬喻更能夠讓人物形象瞬間鮮活。
人生之一切艱難,唯幽默可以消解。有時我會想起古時的蘇東坡,一生以幽默消解苦厄,樂觀迎向蹇途。幽默是詩人天分中最難得的天分。
寫詩,幽默難嗎?這樣說好了……寫詩,一開始我們會花許多年追逐意象(包括各種穎奇詭麗的比喻),只要用功,多仿效,創造意象不是挺難。意象之後,更難的是什麼?是「氛圍」,光影味道和文氣風骨的氛圍,到這階段,我們開始透過斷句、聲韻、運鏡、剪接、結構等等方式去創造一首詩的氛圍(或曰整體的大意象)。
從意象,到氛圍,如果這樣持續十年以上,起碼可以寫出像樣的詩。再後來,我們會發現有些東西是跟天分有關的,並不是想學就成,比如「音樂性」,這裡就要提到瘂弦的詩了,他的詩富於音樂性,這查得到很多論述,就不贅言。但音樂性還是可以學的,只是人人高下境界有別罷了。
有沒有比音樂性更需要天分的呢?有,幽默!瘂弦在〈詩集的故事〉突然寫了這樣一句:「荷馬呢?人們猜測是『幽默』一詞的變調。」或許只是與發音有關,卻引我深思,可以這麼想像,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創作史詩《伊利亞特》和《奧德賽》,背景是暗黑的戰爭,荷馬眼盲的世界亦暗黑,但荷馬史詩最終要說的卻是光明,亦即身為人的堅毅、忠誠,以及熱愛自由的美好德行。暗黑與光明的對比與反差是幽默(諷刺),荷馬是幽默,幽默是史詩的境界。
詩人用幽默銷解暗黑的悲苦,因為,幽默就是一種柔光的悲憫。
瘂弦跟《創世紀》一票戰友都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軍中詩人,辛鬱在《我們這一伙人》開頭這樣速寫瘂弦,「在一九四八年入冬的那段日子,曾經有出生河南省的五千多個青少年學生,在國共戰爭中,顛沛流離,無處安身。瘂弦是這五千多個學生之一,十六歲的他,行囊裡除了幾件破舊衣衫,還有書。」就這樣到了台灣高雄碼頭。瘂弦曾說,逃難時,他沒有帶父母親的照片,竟然帶一本書,那一本書又竟然是何其芳的詩集。
在瘂弦的詩中,大時代的苦難是潛在深沉的背景,愛詩人嚷嚷上口的那首〈鹽〉是悲苦,二嬤嬤反覆嘶喊的「鹽呀,鹽呀,給我一把鹽呀!」聲聲鑽入骨髓。然而悲苦在瘂弦的筆下,往往用幽默自嘲消解,當二嬤嬤叫著給我一把鹽呀,「天使們嬉笑著把雪搖給她」二嬤嬤上吊了,「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嬤嬤」瘂弦詩中無處不在的音樂旋律,彷彿是哀歌,「酸棗樹,酸棗樹/大家的太陽照著,照著/ 酸棗那個樹」(〈乞丐〉),如果人生老吭著哀歌,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呢?面對人生、面對戰爭和艱難的世道,瘂弦的辦法是以幽默來唱、以微笑淺笑搭拉著一把二胡依依呀呀地唱……霧就漸漸散了,天漸漸亮了。
是了,飢饉的日子,「那也不要在麵包裏夾什麼了,╱就夾你的笑吧。」(〈一九八○年〉)笑,在現實生活中瘂弦總是爽朗地笑,在詩中他笑(或許你沒聽見笑聲因著它隱藏在瘂弦小調哀歌旋律裡、笑聲也隱藏在他暗夜壯膽的意象裡),他笑,幽幽默默地,笑是詩意,一笑解千愁或一笑泯恩仇的那種,深刻的詩意。
年輕時我這樣自我提問過,「瘂弦的詩,對於像我這樣一個五年級世代,有什麼啟發?」答案是:「幽默。」我對幽默感的渴求遠高於對詩藝的需要。對人生幽默以對,才會有正能量,幽默是發自內心的微笑,幽默是創意的原型。「工作,散步,向壞人致敬,微笑和不朽。/為生存而生存,為看雲而看雲,/厚著臉皮佔地球的一部份……」(〈深淵〉)這是幽默的態度,詩的態度,或許也是瘂弦的態度。
全文連結:http://okapi.books.com.tw/index.php/p3/p3_detail/sn/3175